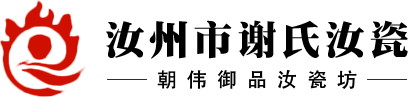

- 服务热线:
- 15037519992---13592175213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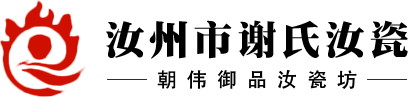

在美的特有尺度下,宋瓷的清隽典雅和明清瓷的华丽繁缛是两种不同的美感,它们有着境界高低的不同。
已故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恰好谈到这两种美感。宗白华先生认为:“些诗如芙蓉出水,颜诗如错彩镂金”(语出钟嵘《诗品·中》颜延之条),这可说是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。
这两种美感或美的理想表现在诗歌、绘画、工艺等各个方面。
楚国的图案、楚辞、汉赋、六朝骈文、颜延之时、明朝的青瓷,一直存在到今天你的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,这是一种美,“错彩镂金,雕缋满眼”的美。汉代的铜器、陶器,王羲之的书法,顾恺之的画,陶潜的诗,宋代的白瓷,这又是一种美,“初发芙蓉,自然可爱”的美。
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,划分了两个阶段。从这种时候起,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,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,那就是认为“初发芙蓉”比之于“错彩镂金”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。
这里指出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一大特点。简言之,这个特点就是重视自然之美和精神之美,而排斥和否定虚华矫饰。先秦诸子如孔丘、老庄等,对美的见解虽各有不同,但在这一点上却是相通的。依我理解,所谓“初发芙蓉”的美,与糅合儒道诸家,强调委婉含蓄、温润和柔的“中和之美”不无关系。
举个例子:李白认为诗贵在清真,正如他在一首诗里说的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饰”。这个意思也可理解为,去雕饰并不是不要美,而正是为了美不被亵玩,钟嵘《诗品》序中说是“不伤真美”。“天然”之美,再要雕饰,那就多余了,过头了。
这个主张其实是与儒家“温柔敦厚”,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,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,“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的思想一脉相承的。儒家要求“美”合乎礼制美学思想体系中,故重“中和”即主张不偏不倚,反对“过”和“不及”。
在我国古代汉民族美学思想体系中,“中和之美”有着更大的包容性和普遍性。还拿李白的那句诗来说,荷花的清真、自然,既是一种美的品格,也可视为一种人格修养的象征。
中和之美”不仅具有审美的价值,而且还具有伦理道德的价值;它不仅体现在美的形式和内容上,还渗透于人的心理,形成一种独特的趣味和审美理想。中晚唐以来,“中和之美”在各种美学思潮中即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。
北宋中期后,经美学风尚的大变革,更被广为接受并深刻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发展,如文人画的兴起、“淡而不伤,和而不淫”之乐风的盛行等。即使在今天,它与许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仍保有一种深层的同构关系。
在世风奢靡的年代,宋瓷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,更能彰显一种文化价值、精神境界和美学追求。这也就不难理解,在精英文化语境中,为什么“初发芙蓉”的宋瓷比之于“错彩镂金”的明清瓷更受推重了。
只是,也应看到,宋瓷和明清瓷代表的不同美感的关系并非对立之两端。我国古代对美的追求和表达是多方面多层次的,“初发芙蓉”的美和“错彩镂金”的美,一直并行不悖且互为周济与参融。这种多样的追求和表达贯穿于整个中华汉民族文化中,体现在同一个文化领域,甚至是同一个“文化个体”——文人身上。
隐逸诗人陶潜,人们都说是他的诗风平淡,可实际上他也有发愤抒怨之作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固然平淡,而“刑天舞干戚,猛志故常在”则不免“金刚怒目”了。
